2025年3月23日,“双体实验室”在深圳举办了《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新版新书发表会,发表会由双体实验室播客主理人林峰主持,本书作者、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金观涛,与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总裁,元宇宙与人工智能三十人论坛理事会理事,双体实验室总顾问余晨展开对谈。
“对创造的渴望”
林峰:《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后来在1983年正式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过一段时间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热”,《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一书可以说是这股潮流的先声。下面我想先请金老师谈一谈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
金观涛:《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是我和华国凡合作完成的,可以说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著作。这本书包含了我们当时对新思想、新道路的追求。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批判自然是有益的,但仅仅有批判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去创造。假定你批判别人的观点,但自己没有新观点,这种批判就是毫无意义的。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刘青峰(编者注:金观涛与刘青峰是夫妻,也是长期的学术合作者)曾负责一个人物专栏的板块,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她以刘宁为笔名写的,谈的是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如何发现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好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态——对创造的渴望。
林峰:这让我想到金老师在《系统的哲学》中提到的一个说法:“控制论运动在中国必定是一个新的创造,而不仅仅是传播……我们当时毫无在学术上建立一家之言的想法,只是一心一意想把问题搞清楚,而忽略了在整个方法的建立上明确区分哪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哪些是自己发现的。我们只是不假思索地把一切归在控制论的旗帜下。其实,这已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控制论!”《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这本书包含了很多金老师和华国凡老师的思想创造,比如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共轭控制”,这个说法在西方控制论学界是不存在的。共轭是一个抽象代数概念,金老师将它应用到了控制论中。
金观涛:是的!在20世纪80年代,我去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国际会议,并将这本书带到了会议上。当时的参会人员中还有一位研究突变理论的专家桑博德博士(Peter Saunders)和遗传学家何美芸博士(Mae Wan HO,华裔英国人,也是桑博德的夫人)。他们对这本书的内容表示很感兴趣。何博士后来还将其译成了英文,但找不到出版社出版,我们想这或许是因为西方人难以理解书中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智慧的例子。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所谈的控制论与西方的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或控制论(Cybernetic)不完全是一回事。
此外,确实像林峰所说,我们当时写作的时候并没有引用规范的意识。《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新版的注释都是在修订的时候补充上去的。如果你们去看过去版本的《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就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注释。学术引用的规范是有意义的,尤其是防止抄袭和剽窃行为。但我们也要有学术创新的自信,没必要为自己的每一个观点都找一个来源或出处。
林峰:刚才金老师提到自己进行控制论研究的时候,包含一种对思想创造的追求。但有一种说法叫“太阳底下无新事”,如何界定这种思想创造或者原创呢?
金观涛:当你产生一个原创性的想法的时候,必须经过两个步骤的检验。第一,很多时候你产生一个想法,但并不一定知道它的重要性。我有很多想法是在朋友们的提醒下,才发现其重要性的。第二,你要相信,很多原创性的想法早就有前人已经提出过了,只是没有得到后世的注意。但这时我们要做的不是引经据典,去维护或论证历史上的那个观点。我们要将自己的观点放到历史上,与前人的说法做出比较。只有经过了这两个步骤,才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原创性思想。
余晨:原创不仅仅是一个最初的想法,还涉及一套落地执行的方案。美国专利局有过一个统计,每一个批准的专利背后都大概有十几个类似的专利。最后到底将专利权批给谁呢?这就取决于谁有更可行的执行方案。还有一个例子,J. K. 罗琳(J.K. Rowling)在《哈利·波特》系列(Harry Potter)出版之后,成为英国首富,这时有好几个人出来告她抄袭。为什么?英语文学发展到今天的成熟阶段,同样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相似的文学创意并不稀奇,但差距在于谁最后将这个创意付诸实施,并发扬光大。
林峰:那么,时隔四十年之后重新审视《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金老师认为这本书完成了哪些有价值的理论突破呢?
金观涛:当时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理论突破的意识,只是想从混沌的处境中跳出来,寻找新的方向。今天来看,这本书在三个方面包含了我的原创性思考。
一是将突变理论作为控制论的组成部分。最初读突变理论创始人托姆(Rene Thom)的《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学》(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我只知道通过结构稳定性可以形成稳态,所有形态的形成都可以由结构稳定性推出。除此之外的内容,我一直读得懵懵懂懂,找研究数学的学者咨询,他们也不懂。最后我一遍又一遍地读,每次读完之后,就将书合上开始冥想,在脑海中构想不同类型的突变机制,才掌握了突变理论。因此,我一直认为数学的研究是不需要语言和文字的,它需要一种特殊的想象力。
二是将控制论思想延伸至认识论研究方面,并逐渐形成从“人的哲学”到“真实性哲学”的系列论述。在西方对控制论的讨论中,人在过去哲学里的中心位置遭到剥夺,但我认为新时代的哲学必须以人为中心。
三是关于信息的说法,我提出信息是可能性空间的缩小,这不是信息论创始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说法,而是我自己的发明。
控制论与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
余晨:《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具有一个特别大的象征意义。当时,世界上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其中控制论的受关注程度,不亚于今天人工智能话题的讨论热度。我的父母亲都是学自动控制出身的,他们对控制论尤其热衷,经常在我耳边说“三论”。控制论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控制论属于交叉学科,并不局限于某个领域内,这使得它能够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奠基性思想之一。就像我们今天谈到人工智能,还会涉及计算理论、哲学、认知科学等。我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当下称呼为“人工智能的时代”。
林峰:余晨说到控制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奠基性思想之一。我想追问金老师的是,为什么控制论是通过转化为一种“科学方法论”——而不是“科学本体论”“科学认识论”,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底色?
金观涛: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方法论的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开始关注的也主要是本体论、认识论。在马克思这里,方法论才被赋予了格外重要的位置,并和他改造世界的理想联系了起来。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三论热”,也有人称呼为“方法论热”。1987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还创办了一本《方法》杂志,专门讨论在社会实践中各种各样的方法。当时的创办者将其定位为“一本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也是一本教育类的杂志”。总之,中国人对方法论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
余晨:除此之外,控制论能够在中国的传播,是不是也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某种亲和性呢?《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来解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
金观涛:《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书中的传统文化案例,主要是华国凡写的。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也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为这本书新版撰写序言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当时我们挑选的案例中,没有一个儒家和禅宗的故事。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是因为中国文明的大传统是道德理想主义,当时的我们希望从这个传统中跳出来。如果你们读过我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会发现其中包含的核心思路就是强调科学理性、反对道德一体化。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是我和青峰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之后,才正式开启的。
至于控制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性确实是存在的。当时最欢迎的控制论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中医。控制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黑箱”,中医不就是一个黑箱吗?华国凡本人就很喜欢中医,他把黑箱理论用到中医研究上。他与我还合作写了一篇讨论中医与控制论的文章,最终在1979年发表在了《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这篇论文后来还在日本《汉方研究》杂志(“汉方”即“中医”)以日译连载。
余晨:伴随控制论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的是信息论和系统论。我们一般称之为“老三论”。在此之后又出现“新三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在西方,很少看到将这些理论捏合到一起的情况,它们在理论逻辑上也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三论”的说法呢?此外,从“老三论”到“新三论”的演变,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思潮变化呢?目前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变化反映人们从关注确定性到关注不确定性,从关注秩序到关注混沌。对此,金老师是否认同呢?
金观涛:我是控制论学者中的“顽固派”。自从控制论诞生之后,虽然各种新的说法、概念层出不穷,但我认为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比如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更多是描述性的,没有提出新的结构。今天对人工智能的讨论也是一样,基本的原理都还是来自控制论。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认为从“老三论”到“新三论”只是一个不断“换新衣服”的过程。
在很多时候,我使用“系统论”“复杂性理论”这些词,更多是为了便于和人们交流,但对其中包含的很多流行说法并不认同。比如,我认为复杂性理论中的“复杂”是一个纯主观的东西。如本书的卷首语所说:“最伟大的东西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它和你自己存在一样简单。”但问题在于,“自己的存在”简单吗?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控制论的理解和接受的着重点不同,而且随着它进入更细分的领域,成为更专业化的东西,这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新的词汇,但万变不离其宗。
从控制论到人工智能
林峰:在金老师的著作中,《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的再版次数是较少的,在1983年出版之后,只在2005年再版过一次。为什么您和华国凡老师会决定在今天推出这本书的新版呢?
金观涛:首先,这是这本书的编辑们努力的结果,我和青峰经常说:“在作者长期探讨写作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的编辑相继付出极大的努力。”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迎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的再版或许有其特殊的意义。人工智能的研究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技术和工程层次的,二是哲学和思想层次的。今天对人工智能的讨论,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改进技术和社会应用层面,忽略了它从控制论转化过来的历史。至于哲学认识论层面的反思则更匮乏了。《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试图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中国读者介绍控制论,从而理解人工智能背后的科学原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落脚点是控制论背后的哲学认识论,可以说它讨论的是一种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方法。因此,我们才决定让这本四十多年前的旧作在今天再版。
余晨:今天,虽然我们很少再提到“控制论”,但它的影响依旧无处不在。控制论的英文是cybernetics,其中cyber就是赛博文化,这是我们至今依旧觉得很酷的东西。我认为,21世纪人工智能的发展,刚好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围绕控制论展开的思想运动。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将当时中国人围绕控制论发展出的思想方法,引向世界。
我想问金老师的是,如果今天您重写《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会有什么不同的写法?过去四五十年出现很多新兴的领域,也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控制论的应用案例。如果我们向前看,还会发现控制论与人工智能将影响很多人类命运的前沿领域,比如生命科学、基因工程、新能源、太空科技等。控制论思想又可能在这些新兴领域内得到怎样的应用?
金观涛:余晨的问题很好,但我暂时没法具体回答,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方向。
《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没有将包含主体的系统与不包含主体的系统区分开来。这两种类型的系统在很多方面是同构的,但依旧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正是我和青峰后来致力研究的方向——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我一直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观念史—系统论”,就是想探索一个有主体的系统如何运行。关于无主体的系统,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神经网络模型甚至能够模拟出这类系统了。然而,对人类最重要的,还是有主体的系统。
我想,相较于思想探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保持思想探索的勇气。今天的世界乱象丛生,从俄乌冲突到新一轮贸易战,很多人都陷入迷茫和焦虑。但“世界还会不会好”是现代人永远面临的挑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方向,今天同样是!我们应该正视当下的挑战,我们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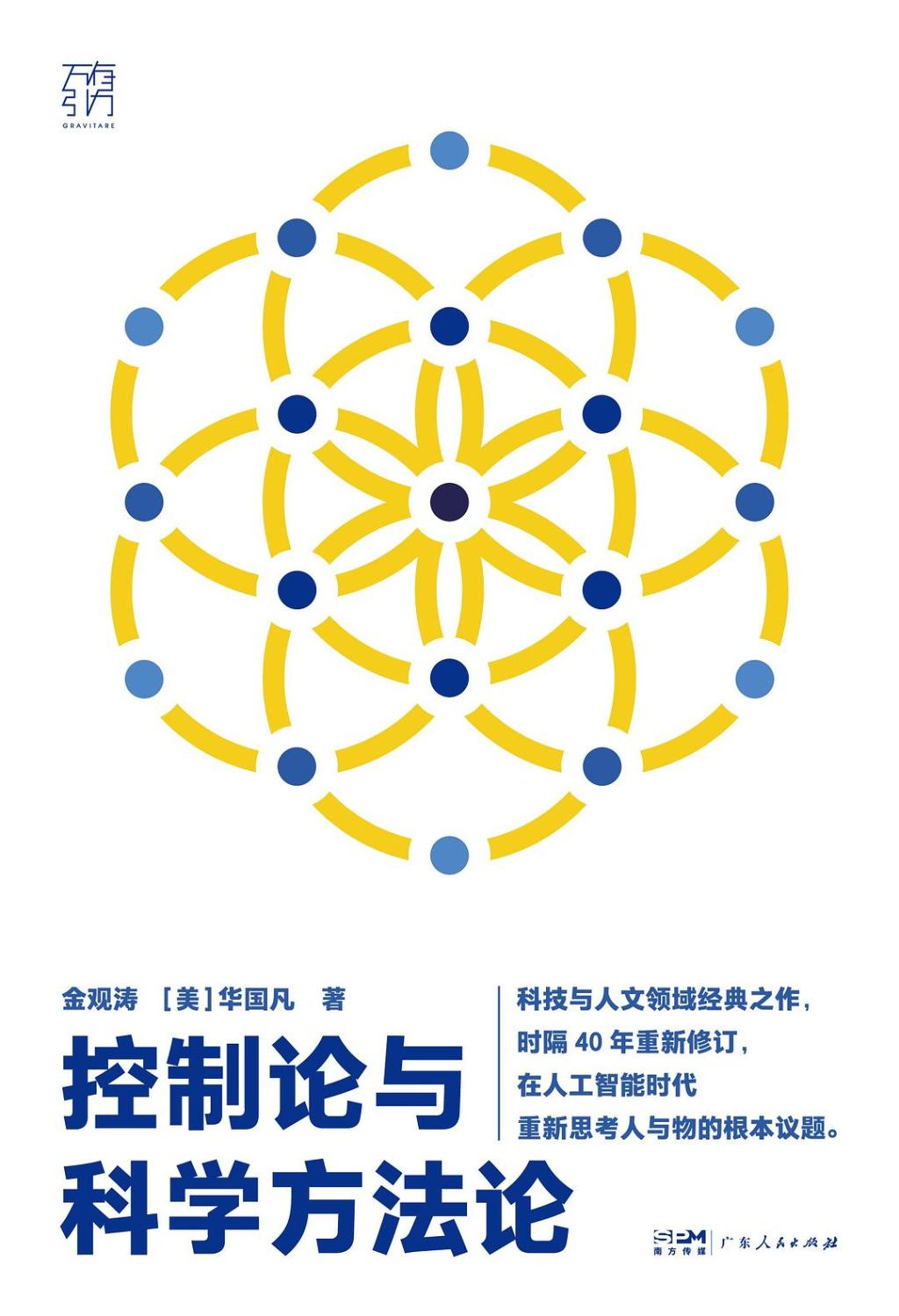
《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金观涛、华国凡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
【本文由宋福杰整理,卜迩编辑。】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家装公司,本文标题:《对谈|金观涛、余晨、林峰:如何在“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时代追求思想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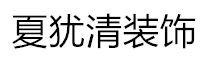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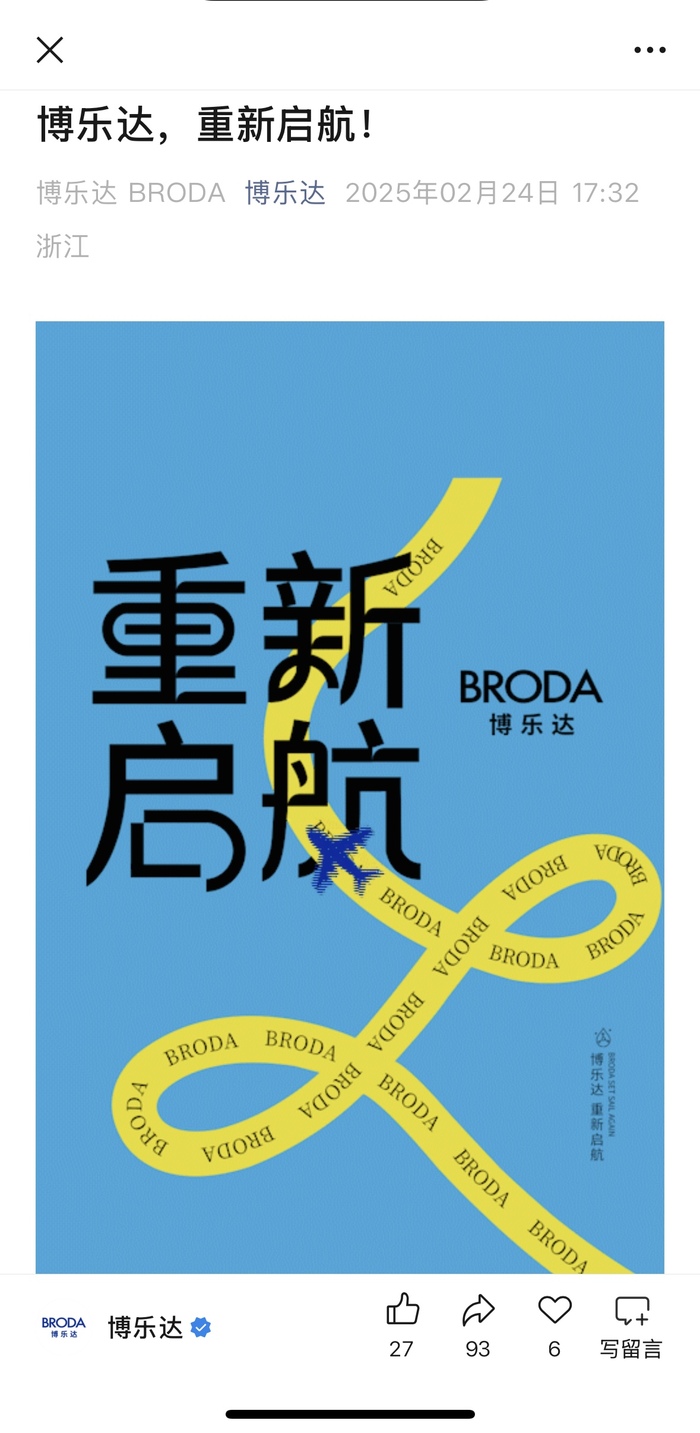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